-
西蒙娜·薇依 编辑
西蒙娜·薇依(Simone Weil,1909年2月3日—1943年8月23日),犹太裔法国哲学家、社会活动家、神秘主义思想家。出生在巴黎一个文化教养很高的富裕的犹太中产阶级家庭。在亨利四世中学曾受教于当时著名法国哲学家阿兰(E.A.Chartier dit Alain 1868—1951)门下,深受其影响。 薇依在亨利四世中学毕业后进入巴黎高等师范学校,1931年获得哲学教师资格,被分配到普伊中学任教。在此期间她开始与工会合作,支持工人罢工,决定过每天5个法郎的生活,以便把大部分工资捐献给矿工互助会。为了确切地考察无产阶级的状况,她认为应该与最贫困的人过同样的生活,于是放弃了舒适的教职到工厂里去做学徒。1934~1936年,她先后到阿尔斯通工厂、巴斯-安德尔冶金厂和雷诺汽车公司去当一个普通工人。她根据自己的切身体验写成的工厂日记在她去世后出版,标题是《工人的状况》(1951),被A.加缪誉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最伟大和最精彩的作品”。1936年西班牙内战爆发,她来到巴塞罗那前线支持共和派的斗争。当战火蔓延到法国的时候,她由于是犹太人而不得不躲到阿尔代什省去当农业工人。1942年她逃出法国到了英国伦敦,参加了戴高乐领导的“自由法国”运动。她夜以继日地拼命工作,加上长期甘于贫困而营养不良,结果被结核病夺去了生命。
中文名:西蒙娜·薇依
外文名:Simone Weil
别名:西蒙娜·韦伊
国籍:法国
民族:犹太人
出生地:巴黎
出生日期:1909年2月3日
逝世日期:1943年8月23日
毕业院校:巴黎高等师范学院
职业:哲学家、作家、神秘主义思想家
代表作品:《源于期待》《重负与神恩》等
信仰:基督教
性别:女
 西蒙娜·薇依
西蒙娜·薇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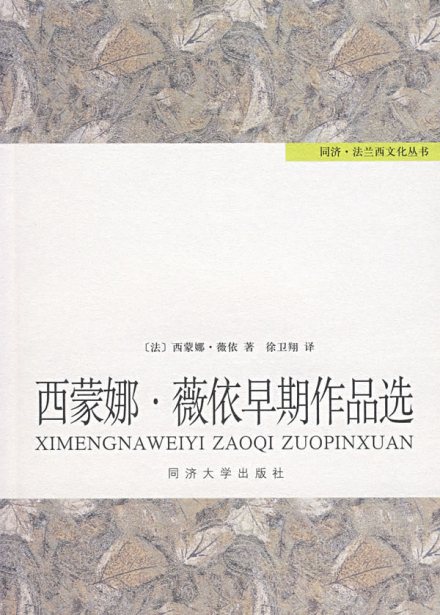 西蒙娜·薇依
西蒙娜·薇依
1942年6月,薇依离开了纳粹德国占领下的法兰西,去了美国,在那里加入抵抗组织。当年11月,她又去了伦敦。在舒曼(M.Maurice Schumann)领导下的部门工作,她坚持要回到法国去执行任务。但考虑她的特殊身份和种族,她提出的要求无法满足。她为了和法国人民同受苦难,坚持严格自律,只消耗在法国安配给票才能够领到的很少的粗劣的食物。加上繁重的劳作,她本来就很软弱的身体很快就垮了下来。1943年8月24日,她终于在英国阿斯福特疗养院与世长辞,年仅34岁。
 西蒙娜·薇依
西蒙娜·薇依
她的哥哥安德烈·韦伊比她年长3岁,在他的帮助下,西蒙娜自幼就获得了文学和科学方面的知识,6岁时,她就能背诵不少拉辛的诗句。第一次世界大战使她的学业经常受挫,尽管如此,1924年6月,16岁时,她终于通过了文科中学毕业会考,成绩是“良”。考试委员会主席是一位中世纪前期文学专家,他在口试时给了西蒙娜19分,满分为20分。
她在维克多·杜吕依中学学哲学,师从于勒·赛纳以后,为进高等师范学校做准备,她在亨利四世中学学习两年,师从阿兰。阿兰发现她有哲学天才,说在她身上具有“罕见的精神力量”,他十分善意地关注着她,但还指出她应当“避免做过于狭窄的用晦涩的语言表达的思考”,并说“她曾经想放弃那种抽象的、深奥莫测的繁琐探求——这对她来说是一种游戏,而进行直接的分析”。
她于1928年考入高师,1931年取得大拿和中学哲学教师学衔,随即被任命为勒浦依市女子中学教师。1931年冬至1932年春,她在那里明确表态反对政府的压制政策,向市政府公开表示对该市失业者的同情并以实际行动援助他们。
她对《无产阶级革命》杂志社深怀友情,1932年开始同该杂志合作。这本杂志使她得以恰如其分地表述人间疾苦,表达她对劳动者处境的基本看法和感情。
1932年10月她被调到奥塞尔,1933年又调到罗昂。这时,她决定告假一年,以便全心全意地体验工人生活,夏天在汝拉山区她在干农活时就想作这种尝试。
她在雷诺厂找到一份工作,在厂附近租了一间房。尽管她息有头痛病,身体又虚弱,但她绝不允许自已的生活条件与车间工人有任何不同。
1935年,假期已告结束,她又重操旧业,在布尔日的女子中学任教,直到1936年夏离开那里。同年8月初,她前往巴塞罗部,她要亲自对“赤色分子”与“佛朗哥分子”之间的斗争作出判断,在数周的时间里,她在卡塔庐西亚前线同共和派军队一起饱受磨难,从内心深处感受到真正的战争灾难。后来,她返回法国。
由于疾病,她再次告假。直至1937年她才去圣康坦女子中学赴任。1938年1月,由于健康状况不佳,又不得不中断教学,直至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
1940年6月13日,她决定离开巴黎,同年10月在马赛暂居。
1941年6月,经女友介绍,她认识了Le. R. P贝兰,当时贝兰正在马赛多明我会的修道院,两年后贝兰被盖世太保逮捕。贝兰又介绍她同G.梯蓬相识,她住在梯蓬家里,在阿尔代什逗留了一段时间。这期间,她经不住农家田间生活的吸引,干起了体力劳动,她帮助收庄稼或收获葡萄,与此同时,她并未放弃希腊哲学或印度哲学的研究,扩展梵文知识,并进一步确定了研究神秘主义和上帝这个概念的倾向,这些研究促使她写下有关天主经和爱上帝的论文。
她在冬天返回马赛,继续同贝兰讨论、研究,在贝兰的要求下,她在马赛多明我会修道院地下小教堂的聚会上阐述自己对柏拉图和毕达哥拉斯学派的看法。
1942年3月,贝兰被任命为蒙佩利耶修道院院长,他从不曾中断同薇依的联系。他们之间的会面,通信和交流只是在薇依离法时才中断。
1942年5月15日前后,她在旅途中写信给贝兰,她称这封长信是她的“精神自传”。轮船于5月17日启程。她在卡萨布兰卡逗留了三周,经法国去美国的旅客都滞留在临时营地里,薇依在那里修改文章并定稿,她把这些文章作为精神遗产寄给贝兰。5月26日她又写了最后一封告别信,对15日的信的内容进行补充和阐发。
1942年6月底,她抵达纽约,法国临时政府委任她一项任务,她于是在11月10日动身去英国。
她在伦敦负责研究条令;她起草计划撰写了一篇有关国家与个人的互相间权利和义务的备忘录。她执意分担仍生活在法国本土的人们所经受的磨难,以至拒绝医生因她过度疲务而特别规定的食品供应,她严格地按照国内敌占区的同胞们的食物配给量领取食品。
她的健康状况严重恶化,1943年4月下半月住进了伦敦弥德赛克医院,8月中,又转到康特群的阿斯福特疗养院。
人们在她的笔记本中发现的最后几个字是:“教学的最重要方面=对教会的认识(从科学意义上说)。”
薇依的整个一生都包含在这个词里。
1943年8月24日,即住进阿斯福特疗养院后不久,她就与世长辞了。
爱中创造一切的上帝
薇依的上帝,不是哲学家和神学家在书斋里皓首穷经研究出来的那个堆砌在一堆玄而又玄的理论背后却从不顾人间疾苦的不动情的上帝,也不是人为了满足自己的私欲而在尘世间苦心打造出来的如贪官污吏一样的偶像。关于这两个方面,都是她尽力拒斥的。她在一篇论及主祷文的文章中写道:“这就是我们的天父;我们身上没有任何真实的东西不来自于他。我们属于他。他爱我们,因为他自爱,因为我们属于他,但是天父在天上,而不是在别处, 倘若我们以为人世间有天父,那就不是他,那是假的上帝。”的确,从薇依的信主经历和她的哲学背景出发,我们发现她很注重上帝的超越性,这是和她面对时代的环境而分不开的,她必须回应当时欧洲把社会运动神化、把国家神化、把德意志民族神化的思潮,而且,欧洲的问题就在于取消了基督教传统中上帝的超越性,取消了神圣与世俗之间的差别,神圣者不再神圣,俗世反成为神圣。所以,她一针见血地指出:“我们时代的谬误乃是由于无超自然的基督教。政教分离论(le lacisme)是原因——首先是人文主义。”甚至于她把上帝的超越性提高到一个认为上帝是“与超自然无形地隐没在宇宙中”而且“他们无形地隐没在灵魂中,是件好事。”因为这避免了把不是上帝的东西当作上帝来敬拜,也许薇依并没有想要和什么思潮作战,但她很清楚,离开了上帝的超自然性,偶像崇拜必然产生。表面上看起来,薇依的上帝有些如哲学家的形而上学中构筑的“太一”“绝对理念”等概念,加上薇依的良好哲学素养,有可能使人怀疑这位上帝还是不是那位永活的上帝,那位造物的主宰,薇依是否矫枉过正?但薇依自己就在她的作品中回答了这样人的提问。她的上帝不是不动情的上帝,相反,她的上帝不仅坐在高天之上,而且还俯视愁苦的群生并自愿来到他们中间,与他们同受苦难,这一切都是因为他是爱。薇依写道:“上帝穿过茫茫尘世来到我们这里”。而且,这位来到我们中间的上帝是一个“出于爱心,为了爱而创造……只创造爱本身和爱的手段而没有创造它物”的上帝。
上帝的爱是他属性的首要,“首先,上帝是爱。首先,上帝在自爱。这种爱,上帝身上的这种友谊,就是三位一体。”这种作为位格与位格之间的联系的爱,是薇依上帝观的出发点。可以看到正是在基督教悠远绵长的两千年历史中,薇依所属的神秘主义传统对上帝圣爱的属性一贯的强调。显然,爱不仅是神秘主义传统的核心概念,也是基督教信仰一贯的核心概念。上帝是爱是不言而喻的真理。从中世纪的神秘主义者们的作品中屡屡可见他们特别的强调。如著名的13世纪女神秘主义者哈德薇希认为爱比天地所能包括的一切事物都更为宽阔和辽远,更为高深恒久。上帝之爱超越一切。而另一位极负盛名的吕斯布鲁克则说:“……一切事物在圣灵的溢流中都被圣父和圣子全新地爱着。这就是圣父与圣子的行动着的相遇;我们在其中,在永恒之爱中通过圣灵而被充满爱意地拥抱着。”薇依继承了这一神秘主义者们对上帝的认识并有她自己的理解,她把上帝的爱直接和上帝的创造放在了一起:“一切存在之物在其存在当中,也同样受到上帝创造型的爱的支撑。”同样,作为上帝的朋友,应当“热爱存在之物,以使他们对尘世间万物之爱同上帝之爱交融”。可以说,与某些人想象的相反的是:不把上帝与上帝的创造分割,而是从万物的美善看到上帝的爱,这是基督教神秘主义的主流。
不幸的意义:基督的十字架
薇依的上帝观不仅强调上帝的爱,更强调这位爱人的上帝爱人到一个程度,竟然参与了人的受苦。受苦的上帝是20世纪神学思潮的一大主题,许多神学家用头脑来思考上帝的受苦,以期待给世界的苦难一个答案。而薇依则是身体力行地与这位受苦的上帝站在了一起。从她自己切身体会出发认定受苦的上帝就是那位在十字架上的上帝。在她的神秘经验中“当基督突然降临我身时,无论是感官还是想象都不曾有任何参与;我仅仅在苦痛中感到某种爱的降临,这种爱就像在一位亲切的人脸上所看到的微笑。”
在苦痛和不幸中,薇依看到了基督信仰的真实性。人们都知道:自宗教改革后,路德所提出的“十字架神学”很大程度上表明了上帝在基督里为我们的缘故承受苦难与不幸这一既旧且新的教义。当路德论到上帝如何分担基督的苦难时,他明确地用上了“被钉死的上帝”(Deus Crucifixus)一词。基督的受难与不幸很大程度上就是上帝的不幸与苦难,在不幸与苦难中,上帝的爱以非同寻常的方式临到了人类。而薇依也说:“十字架上受难的最崇高时刻的从容,两边是何等爱的深渊!”
人们都知道,自从莱布尼茨提出神正论的问题之后,围绕着全能全爱的上帝为什么容忍罪恶与不幸存在于世界之上,不知伤透了多少神学家、哲学家的脑筋,反宗教的人士更是以此为借口来抗议让人受苦的上帝。可以说,在基督教现代思潮中,神正论问题是一个必须面对而不容回避的问题。薇依由其神秘主义的立场出发,力图在基督与人的相遇中,在亲身体验人的不幸与苦痛中寻找答案。
薇依和其他基督教思想家略有不同的一点是她竟然认为不幸是绝对的。作为存在的人的不幸是无法消除的。她说:“不幸:时间把有思维的人,不管其意愿如何,带向她无法承受但却必然会来临的东西那里。”刘小枫博士对此的解释是:“这意味着人通过任何手段都无法最终消除生存之不幸……由偶然性导致的不幸与人与生命会共存。悲凉永远会伴随着人的存在之偶然性,伴随着人的遗憾。”而且,薇依坚决拒斥不幸也会给人带来益处的这种所谓锻炼的学说,她认为罪恶和痛苦如果被人感知到其益处或能引起崇高的光荣的话,那它就不是不幸。不幸之所以是不幸就在于它是对生活的一种彻底否定,是降临于某人并把它彻底摧垮的事件。最大的不幸,就是上帝的不在场。使一切都变成虚空而无意义。因此薇依从不把基督信仰当作对苦难的逃避或麻醉——正如马克思所认为的那样。相反,她认为就是基督也同样地遭遇不幸,而且是遭遇到人所不能忍受的最大的不幸,上帝在基督里倒空自己,上帝不在场了。所以他在十字架上大喊:“我的上帝,我的上帝,你为什么离弃我!”但上帝的爱从此就显明出来了,基督的受难成为了另一种“赐福的不幸”。在这种不幸当中,上帝把自己的存在倾空。这种倾空显明了上帝在生存破碎中去爱的无限奥秘。这样,每一个执着最求爱的人应当在不幸中来与上帝站在一起,与十字架上的基督站在一起,直至灵魂和基督发出同样的呼喊,在这种情况下,他才会真切地感受到上帝是多么地爱世人,这才是真正地爱上帝的人,而基督徒正是这样的人。这就是为一所说的“相似于上帝,但是在十字架上受难的上帝……因此,一个爱人的上帝,一个爱上帝的人,应该受苦”的真正含义。
不幸可以说是没有意义的,因为它意味着上帝不在场从而取消了一切生存的意义;但不幸在基督的十字架上又被赋予了意义,因为它意味着从极度的十字架被树起的那一天起,上帝的爱穿越了一切深渊来到了不幸的人之中。“必须在虚无和虚空的苦难中努力找到更为充实的现实,同样,应当热爱生活以更加热爱死亡。”这也许是对薇依和像他一样千千万万的基督徒的生活的最好注解。
“涤罪的无神论”与“教外基督徒”
薇依的信仰一直备受争议。最大的原因可能就是她一直未接受洗礼并且是主动拒绝接受洗礼,虽然她表明自己很热爱宗教仪式对此并不感到反感。相反她多次参加弥撒和节期活动。并在其中得到很多精神上的帮助和满足,从现有的资料来看,我很怀疑她是否在没有接受洗礼的情况下去领过圣餐。而且,有的人还不敢肯定薇依是否有“得救的确信”。因为薇依在自己皈依后也曾说过:“真实的矛盾状况。上帝存在着,上帝并不存在。”并且她还肯定有一种“对上帝这个概念净化的无神论”在某些人看来,薇依不仅不是一个基督教的会员,恐怕连是否认信基督都很成问题。她不仅给无神论说话,甚至还替佛教、印度教、希腊神话的众神来寻找信仰的根据,在她给一位修士的信中这样写道:“基督教诞生以来,除在天主教教会之外的那一部分人(“不虔诚的人”“异教徒”“不信教者”)也有对上帝的爱与认识。更广义地讲,认为从基督教诞生以来,在基督教民族中比某些非基督教国家,例如印度对上帝拥有更多的爱与认识,这种说法值得怀疑。”在这封信中,她详细地比较了各种宗教的学说和思想,深刻地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如若我们明白了希腊几何学与基督信仰是从同一源泉喷发出来的,那我们的生活将会发生多么大的变化啊!”来读薇依的这些文字,也许有的人会愤怒、会瞠目结舌、会反感……但没有人会否认这些文字下面是一颗跳动的质朴真实的良心。
事实上薇依不是一名传统意义上的基督教徒,但她绝对是一名跟随基督的基督徒。她用自己的声明告诉人们一个真理,在有形的教会之外,上帝仍然做工。下面来看看她的所谓的“无神论”和拒不受洗到底是怎样一回事。不是替她解释和辩护,乃是要让我们触摸这美丽的灵魂。
在一开始就必须明了:薇依的认信完全是从其生存的不幸处境中与上帝相遇的,不是任何的教条学说,也不是哲学理念。这就决定了她必然是一个真切地在生命中体会和跟随基督的人。决定了她必然是一个神秘主义者。
薇依之所以写出上面那段对上帝的存在似乎不确定的话语,乃是她从人的生存处境出发真实地思考,一方面她知道对于理性的头脑来讲,接受超自然的存在是一件多么困难的事情。“我坚信并无上帝,则是从这种意义讲的,即我确信没有任何实在的东西相似于我说出来的这个名字所可能设想到的东西。”随后,她更加坚定有力地说出:“但是,我无法设想的东西并不是幻想。”读到这里就恍然大悟了,可见薇依不是否认上帝的存在,薇依从小受到良好的理智上的训练,对数学、逻辑、语言、哲学都有很高的素养,她并不是否认理智对人的益处。乃是用理性在说明理性在证明上帝是否存在问题上的无能与无助。靠理性证明上帝,此路不通也。
同时薇依以一种特别开放的态度看待无神论。她这样写道:“有两种无神论,其中之一是对上帝这个概念的净化(purification)。”“在两个不曾体验过上帝的人中间,否认上帝的人也许离上帝最近。”薇依此话不无道理。她又说:“虚假的上帝在各方面类似于真的上帝,除非人们不去触及他,不然他会永远阻止人们接近真正的上帝。”其实,薇依的所谓的“涤罪的无神论”并不是指她要抛弃上帝,乃是指她要抛弃那人为的虚假的上帝的概念,比起无神论者,特别是真正肯于在世界上追求公正、良善和一切美好的无神论者,那些虚假的信仰者更加远离上帝。
薇依拒不接受洗礼,这是来自于她对教会及人为的制度的一种深刻的体会。她在讲述她为何不接受洗礼加入教会时说:“我想,无论在什么情况下,我将永不会入教,为的是不因宗教而使自己与普通人相隔。”她认为教会作为尘世间的一个社会组织而存在,就不可避免地具有“滥用权力的天然倾向。”而在教会的历史上,教会犯下了许多错误:以宗教的名义发动政治战争,逼害异端,压迫各社会阶层。作为一个局外人,她痛苦地看到在教会当中,参杂了许多人为的因素。“除了纯粹的神秘主义外,罗马的偶像崇拜把一切都弄污了。”
对于教会外的真善和美好,薇依从来不会加以否定。她认为这同样是来自于上帝的创造。她深刻地指出:“有这样多的事情是在教会之外,使我所爱和不愿意放弃的,这些事情一定是天主所爱的,否则它们不会存在。……这一切常被教会贬低,其实不是完全没有价值的”而这些事情包括了“希腊、埃及、古印度和古中国,世界的美,在科学与艺术中反映的这些纯净朴实的美。……我甚至还可以说得更多。总之,是对表面化的基督宗教之外的这一切之爱,使我停留在教会之外。”但停留在教会之外不意味着在基督之外,薇依以她自己的实践告诉人们,她一直在爱与不幸当中期待上帝的降临。

源于期待
作者名称 西蒙娜·薇依
作品时间2009-1
《源于期待》是2009年1月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图书,作者是西蒙娜·薇依。

在期待之中
作者名称 西蒙娜·薇依
作品时间1997-01
《在期待之中》是1997年三联书店出版的图书,作者是薇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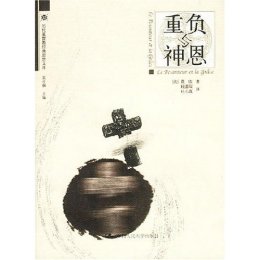
重负与神恩
作者名称 西蒙娜·薇依
作品时间2003-10-01
《重负与神恩》是一本2003年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图书,作者(法)薇依,顾嘉琛,杜小真 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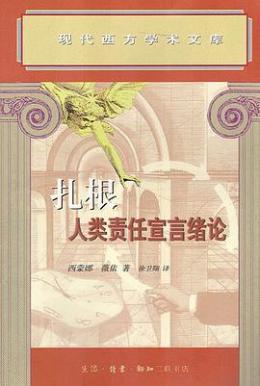
扎根
作者名称 西蒙娜·薇依
作品时间2003-1
本_包括:_魂的各_需求、拔根__、扎根等三部分_容。
首先,对于基督教的神秘主义传统,有许多人,特别是教外的人总认为是消极遁世,逃脱现实的一种信仰。薇依用自己的思考和实践对这种看法的错误提供了最好的反驳。她认为上帝让我们爱这“故土”的世界和世界上的美。薇依自己以身作则,亲自参加工厂的劳动,和劳苦民众同甘苦共患难;在民族沦亡之际,她挺身而出,在国外参与抵抗运动,直至积劳成疾,早逝于贫病交加之中。她的生命和思想,深深地影响着当代的基督教信仰。正如玛多勒所说:“能够改变一种生活的书是很少的,薇依的书就属于这类书之列。在读了它的书之后,读者很难保持读前的情况……”以至于人们把她的《重负与神恩》的书与帕斯卡尔的《思想录》相比较,并称她为“当代的帕斯卡尔”。我想是不过分的。
其次,对于人们如何看待痛苦与不幸。薇依的思想使人们得到了更好的启发。“一个充分和合理的神义论必然要求上帝最终对世界的苦难负责任,而满足此要求最有力的证明,便是上帝在苦难中有份。”传统基督教教义坚持上帝不懂情性的观念,事实上是受到希腊哲学的影响。20世纪以后,随着苦罪问题日益成为基督教神学的重要关注。薇依和其他在实践中经历上帝与他们一同受苦和战胜罪恶的思想家们共同得出了上帝在苦难与不幸中与人相遇,并与人一同承当苦难的后果的观念,使基督教神学在启示之光的照耀下勇敢地面对和回应苦难对人的威胁和攻击,并及时给在受苦当中的人以慰藉和希望。在谈到十字架神秘主义时,当代神学家犹根·莫尔特曼深刻地指出:“通过基督的受难与死,耶稣认同于那些被奴役的人,分担他们的受苦。…他们在自己遭受奴役的痛苦中也没有被抛弃。耶稣与他们在一起。在耶稣中,他们得到解救的希望;耶稣的复活与进入上帝的自由中,为他们带来自由的希望。在一个剥夺了他们所有希望,剥夺他们所有人性身份,直至它不可再见的世界里,耶稣使他们认同于上帝。”假如薇依看到这段话,一定会表示非常赞同的。
最后,薇依对待教会之外的真善美的看法。对待所谓的“无神论”的认识,也给人们一个很好的提醒。当然,自始至终薇依都不是一个无神论者,更不是一个异教徒。她是一个彻底追随基督的人。她从未否认基督救恩的真实性和独特性,她说:“没有重生,没有内心顿悟,没有基督和上帝在灵魂中出现,就不会获救。”但她仍然对这世界上的美好和那些崇高道德的无神论者或其它宗教的信徒抱有崇高的敬意,她相信他们不在上帝的恩典之外。她认为那些拥有超自然的爱和接受上帝所创造世界秩序的人“即使作为无神论者而生而死,他们也是圣人。”在一个周围几乎都是非信徒的社会当中,基督徒如何看待他们?如何看待教会之外的真实和美好?是自以为义画地为牢还是敢于肯定上帝的工作和他在这个世界中默默无声于那些一直在痛苦中而并不屈服的人们站在一起?无疑薇依会给人们提供一个思索的线路。
当然,薇依的思想丰富异常,可能要继续讲下去的话还会有很多未能发掘出的珍贵闪光之处,但限于时间和篇幅的关系,只能讨论到这里。最后我们愿意随着薇依在世时的一次经历来结束本文,让我们再一次和这位伟大而美丽的心灵共同去感受那位爱我们的上帝的爱。
他(圣神)带领我到一间教堂(1942年在马赛)。教堂很新但很丑陋。他对我说:“跪下。”我回答说:“我尚未领洗。”他说:“带着爱跪在这块土地上,就像你跪在一个维系着真理的地方一样。”我服从了。
人们在她的笔记本中发现的最后几个字是:“教学的最重要方面=对教会的认识(从科学意义上说)。”
薇依的整个一生都包含在这个词里。
1943年8月24日,即住进阿斯福特疗养院后不久,她就与世长辞了。
她曾说:“我们生于他人的苦难里,而死于自己的痛苦中。”这也是她精神的写照。
西蒙娜从民主主义、和平主义、社会改良主义向宗教救世思想的转变,深刻反映了资本主义社会中知识分子的痛苦、迷茫、奋斗和思考。
西蒙娜拥有特立独行,自甘苦行、永远站在穷苦人民一边的“圣女”人格和感人生平,她的思想充满智慧。
源于期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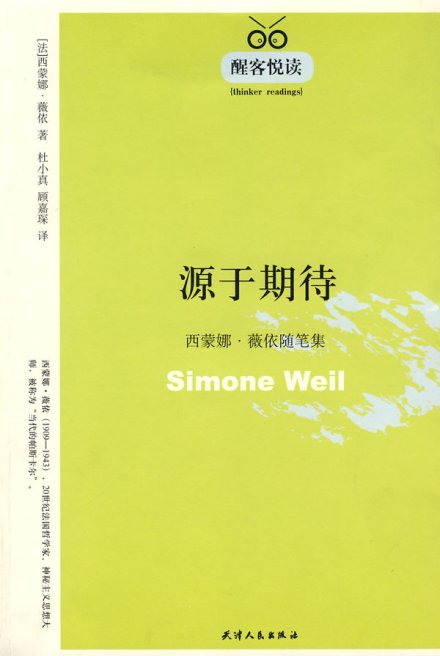 源于期待
源于期待
01 论无辜者的不幸
02 论必然与顺从
03 灵魂朝着上帝
04 注意力的质量
05 最可贵的财富不是寻找得来的
06 只有正义才使意志和谐
07 聆听一个不幸者的声音
08 感谢那些并不知把面包赐予谁的人
09 爱世界的秩序
10 美是世间唯一的合目的性
11 肉体之爱意欲世界之美
12 共同的光明普照众生
13 爱宗教礼仪活动
14 目光注视着完美的纯净
15 神圣的东西无须费力
16 作为人类之爱的友情
17 内在的爱和外露的爱
18 重负与神恩
19 虚空与报答
20 接受虚空
21 超脱
22 填补虚空的想象
23 弃绝时间
24 无对象的渴望
25 我
26 失去创造
27 隐没
28 必然与服从
这本书是薇依的一些随笔。她的文字有一种非同一般的美。这种美让我们怀疑她的存在是否真实。薇依的思想不同于任何人。是的,她是上帝疯狂的热爱者,追随者……这给了我们一个很好的理由来解释她文字中令人无法想象的绝对性和冷漠感。
以下是我摘抄的几句,希望大家能有所感触:
1 人们只有在某种距离上看待不幸时才可能接受不幸的存在。
2 爱真理意味着接受空虚,继之接受虚空,继之接受死亡。真理是同死亡在一起的。
3 依恋并非他物,只是现实感情中的不足,人们依恋与对事物的拥有,因为人们以为若不再拥有此物,就不再继续存在。许多人并没有以全部身心去领会,在一个城市被毁灭和他们一去不复返地远离这城市之间截然不同。
4 凡是存在的东西绝对不值得爱。
因此,应爱不存在之物。
但是,这个不存在的爱的对象物并不是想象的。因为我们的想象不可能比我们自身——我们自身并不值得爱——更值得爱。
5 美,是一种人们看着它而不向它伸手的水果;
同样是一种人们看着它而不退却的不幸。
6 有一种不幸是:人们无力承受它延续下去,也无力从中摆脱出来。
7 限定是上帝爱我们的证明。
……
这本书是令我对薇依感兴趣的原因。她不像想成为天使那样去爱上帝,她对上帝的爱是摒弃。
重负与神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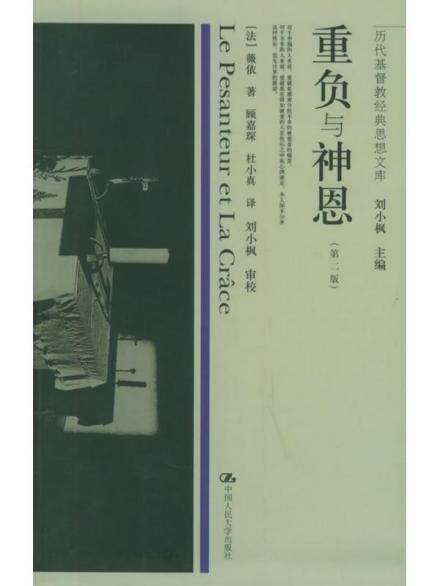 重负与神恩
重负与神恩
1、本站所有文本、信息、视频文件等,仅代表本站观点或作者本人观点,请网友谨慎参考使用。
2、本站信息均为作者提供和网友推荐收集整理而来,仅供学习和研究使用。
3、对任何由于使用本站内容而引起的诉讼、纠纷,本站不承担任何责任。
4、如有侵犯你版权的,请来信(邮箱:baike52199@gmail.com)指出,核实后,本站将立即删除。
下一篇 克劳德·德布鲁
上一篇 路易·皮埃尔·阿尔都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