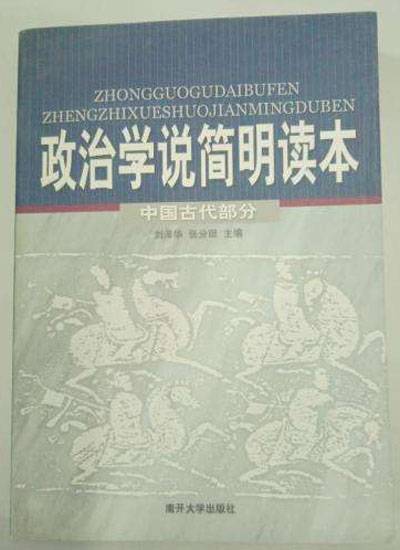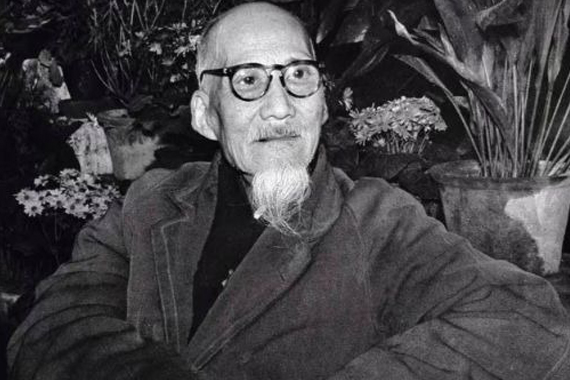-
政治学说 编辑
政治学说是关于政治思想和政治哲学的一些言论,不形成价值判断而去研究社会现象。
中文名:政治学说
提出:利奥·斯特劳斯
属性:治制度确立了标准
特点:不形成价值判断而去研究社会现象
政治学说都必须涉及到目的,并在阐述全然是政治性的目的时,还为评价政治行为和政
治制度确立了标准。再者,政治哲学是一个更大的整体的一部分,即哲学,或“寻求智慧”的一部分,亦即“寻求普遍性知识,寻求知识的总合”的一部分。 因此,就政治哲学而言,“就是试图真正了解政治事务的性质以及正确的或完善的政治制度这两方面的知识”。 在第一部分导言评论中,政治思想必须既涉及到被称之为政治理论的一方面(试图真正了解……政治事务的性质),也要涉及到被称之为政治哲学的另一方面(试图真正了解……正确的或完善的政治制度)。简言之,政治学说离开政治哲学是不可想象的,“一般地说,不从政治哲学上做出评价,要对思想、行为或工作有所理解,是不可能的”。 什么是政治哲学?斯特劳斯教授按照运用某一种或另一种概念的结果,尤其根据“社会科学实证主义”和“历史循环论”的角度来判断(斯特劳斯认为后者是“政治哲学不可忽视的对抗者”),并通过对“古典政治哲学”的概括和引伸,从而回答了这个问题。在什么是政治哲学的问题上,斯特劳斯与萨拜因的不同之处就在于他把自己的见解更多地建立在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哲学上;他也不同意卡特林的建立在社会学和美学基础上的政治思想。
现在不必在这里对社会科学实证主义理论上的缺点进行讨论,只要提一下明确反对这个学派的一些想法就够了。 (1)不形成价值判断而去研究社会现象,即一切重大的社会现象,是不可能的。一个对那些把视野只局限于自己的食品消费和消化力的人们采取鄙视态度的人,可以是一位较好的经济学家,但他对人类社会的特征就说不出什么道理来。一个拒绝把伟大的政治家、平庸的人和愚蠢的骗子加以区分的人,可以是一位优秀的目录学家,但他不能在有关政治和政治历史方面发表出什么高见。一个不会把深奥的宗教思想与衰落中的迷信活动加以区别的人,可以是一位优秀的统计学家,但他在有关宗教社会学方面却可能不置一词。 一般说来,了解思想、行为或工作而不对之做出评价是不可能的。如果我们不能适当地做出评价,如我们经常所作的那样,我们就不会恰如其分地在理解上取得成就。不让从前门进入政治学、社会学和经济学领域的价值判断,却从后门进入了这些学科:这些价值判断来自被称为精神病理学的当代社会科学的附加物。社会科学家认为,由他们来谈论精神错乱、神经过敏和不适应环境的人,是不得已而为之。但是,这些价值判断同伟大的历史学家们所运用的价值判断是有区别的。 其区别并不在于这些价值判断具有较大程度的明确性或肯定性,而恰恰在于它们缺乏判断力:一个圆滑的活动家可以和一个好人或一个好公民同样地适应生活,甚至适应得更好。 最后,我们不应忽视无形的价值判断,即隐藏在缺乏识别力的见解之中,但据说在纯叙述性的概念方面依然是非常有用的价值判断。例如,当社会科学家区分民主的特性与独裁主义的特性或区分人类存在的类型时,据我所知,他们所谓的“独裁主义者”从各方面来看就是一幅讽刺画,一幅作为某一类好的民主主义者对它的一切都要加以非难的讽刺画。再如,当他们谈论合法性的三原则,即理性、传统和神授能力时,正是他们运用的词汇“神授能力惯例化”表现了新教徒的或自由主义的偏向,而这种偏向是没有一个保守的犹太教徒和天主教徒会接受的。 根据“神授能力惯例化”的概念,一方面海拉卡的起源出于圣经的预言;另一方面天主教会的产生则出于新约教义,这两方面都必然表现为“神授能力惯例化”。如果应该提出反对的话,那就是价值判断在社会科学中确实是不可避免的,但它仅仅具有条件的特征。 关于这一点,我愿作如下回答:当我们对社会现象发生兴趣时,难道无需具备有关条件吗?难道社会科学家不该像医学那样必须提出健康与长寿是有益的假设,也要提出在这个世界里一个健康的社会生活是有益的假设吗?再者,只要我们把事实作为事实(例如,具有起因的事件的“事实”)来对待,难道一切事实的论断不也是以尚未成为问题的条件或假设为基础的吗? “没有价值”的政治科学是不可能的,这一点可以简单说明如下:政治科学是以政治事务与非政治事务之间的区别为先决条件的,因此它包含了对“什么是政治”这个问题的某种回答。为了真正成为科学,政治科学必须提出这个问题并给予明确、适当的回答。 但是,要给政治下定义是不可能的,也就是说,在以相应的方式涉及到城邦、“乡村”或“国家”时,如果对这类社会的构成是什么这个问题避而不答,是不可能的。只给社会下定义而不涉及它的目的性也是不可能的。多数知名人物试图给国家下定义而不联系它的目的,这就导致一种从“现代国家类型”中抽取出来并只能适用于那个类型的有关国家的定义,这是为大家所公认的。 这种作法只不过是先不限定国家的意义就去解释现代国家的一种尝试罢了。但是,通过解释国家,或更确切地说解释国内社会,并涉及到它的目的,人们就承认了一个必须借以评价政治行为和政治制度的标准,即必须把国内社会的目的作为评价国内社会的标准。 (2)否定价值判断是建立在认为人类理性不能从本质上解决不同的价值观念或价值体系之间的冲突这种假设之上的。但是,这种假设,尽管一般说来已得到充分确认,却从来没有被证实过。要证实这种假设,需要做出注入如《纯理性批判》一书中概念的形成和详尽的阐述那样大的努力;需要对理性的评价做出综合的批判。 然而实际上我们看到的只是一些肤浅的言论,并妄图用来证明这个或那个特定的价值冲突是无法解决的。表示同意有人类理性实际上不能解决的价值冲突,这是慎重的态度。但如果我们不能确定云雾覆盖着的两座山中哪个山顶高一些,难道还不能确定一座山比一个鼹鼠丘要高吗?如果我们不能确定几个世纪以来彼此一直在打仗的两个邻国之间的战争哪个国家的起因要正义些,难道就不能断定那个无耻的放荡女人对拿伯***的行为是不可宥恕的吗? 社会科学实证论之最大的代表人物马克斯·韦伯就是以各种价值冲突的无法解决为出发点的,因为他的心灵渴望有一个世界,在这个世界里,强力的罪恶同更加强有力的信心交织起来的失败情绪,取代了幸福和安详而成为人的崇高的标志。归根结底,价值判断不受理性制约的信念鼓励了对有关正确与错误或好与坏做出不负责任论断的倾向。人们回避认真讨论这些严肃的问题,并用简单的办法把这些问题作为价值问题打发掉。人们甚至还制造这样的印象,即一切重大的人类冲突都是价值冲突,然而,至少习以说,许多这类冲突的引起正是出于人们在有关价值的看法上的一致。 (3)相信科学知识,也就是说相信现代科学拥有的或追求的知识是人类知识的最高形式,这就意味着对前科学知识的贬低。如果考虑到当今世界的科学知识与前科学知识的巨大差别,人们就会认识到实证主义是以毫不隐晦的方式保留了笛卡尔对前科学知识的普遍怀疑以及他从根本上与前科学知识决裂的情况。 实证主义肯定怀疑前科学知识并把它和民间传说相比。这种迷信行为鼓励了各种毫无效果的调查或令人难解的极端愚蠢的行为。每个具有正常智力的十岁儿童所理解的事物被看作是需要加以科学检验的事物,以便成为可以接受的事实。但是,进行这种科学检验不仅是不必要的,甚至也是不可能的。我们可以用最简单的例子来说明这个问题。社会科学领域内的全部研究工作推测出它的爱好者可以把人和其它动物区别开来,这个最起码的知识不是他们在教室里学到的,也不是由社会科学使之变为科学知识的,而是全然没有作任何修改地保持了它的最初状态。如果这种前科学知识不是知识,那么一切同意或反对它的科学研究也就都不具有知识的特征了。致力于对每个人都已充分地和很好地了解而无需加以科学检验的事物进行科学检验,就会导致忽视必然是先于一切科学研究的思想或见解,如果这些研究是适当的话。 政治科学的研究经常被描述为从查清政治“事实”即迄今为止政治上所发生的事,上升到形成用来对未来政治事件做出预测的“规律”。达到这个目标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但既不事先调查一下究竟政治科学论述的题材是否可以用“规律”这个术语而得到恰当的理解,也不调查一下究竟政治事务的真相是否能通过普遍性的规律来理解,而普遍性的规律是不能以完全不同的术语构想出来的。 涉及政治事实、政治事实的关系、经常发生的政治事实的关系或政治行为的规律的科学,需要超脱正在研究的现象。然而如果这种超脱不会导致不相干的或使人误解的后果,人们就必须看到寓于整体中的被谈论的现象,并且必须阐明那个整体,即阐明整个政治或政治社会制度。例如,如果不考虑政治制度的种类是以究竟是否存在“集团政治”为前提的,也不考虑特定的“集团政治”事先假定的政治制度,人们就不会获得一种值得称之为关于“集团政治”的科学知识。但是, 如果人们对民主的可供选择缺乏明确理解,也就不可能阐明具体民主或普遍民主的特征。 科学的政治学家倾向于只把民主与独裁主义加以区别,也就是说继续保持在特定的政治制度及其对立面限定的范围之内把特定的政治制度绝对化。科学探讨容易忽略最主要的或基本的问题而不假思索地接受已经认可的见解。 对于这些基本问题,科学上严谨的朋友却很不严格,这里再次提出最简单的同时也是最明确的例子:政治科学需要阐明政治事务与非政治事务之间的区别;需要提出和回答“什么是政治”的问题。这个问题不可能科学地加以论述而只能辩证地论述,而辩证地论述则必须从前科学知识开始,并且最认真地加以对待。前科学知识或“普通常识”之类的知识在哥白尼和随后的自然科学领域看来是不可信的。但是,我们可以称之为宏观—微观的知识,在某些领域中是非常丰富的。 这一事实就使人们无权否认只存在可以看到它们的情况的事物,如果是以不挑剔的眼光或更确切地说是以平民的、有别于科学观察者的眼光去看问题的话。如果人们否认这一点,就会重复格利佛 在大人国碰上护土的经验,并卷入像使格利佛**** 在拉普达感到惊讶的那种研究项目中去。 (4)实证主义必然使其自身转变为历史循环论。由于受自然科学模式的制约,社会科学正处于犯有把美国二十世纪中期或更普通地说是把当代西方社会的特征当作人类社会的主要特征这种错误的危险之中。 要避免这种危险,社会科学就得被迫去从事“跨学科的文化研究”,从事对当代的以及历史的两方面的其它文化的研究。但社会科学在进行这种努力时,却误解了其它文化的意义,因为社会科学是通过起源于当代西方社会、反映这个特定的社会并只能完全适用于这个特定社会的一种概念组合去解释其它文化。 要避免上述危险,社会科学必须像它们理解或已经理解自己那样去理解这些文化。社会科学所需要的主要理解方法是历史的理解方法。历史的理解方法已成为事实上的经验主义的社会科学的基础。但如果考虑到理解历史的任务之大,人们就会开始怀疑历史的理解是否取代了对于社会的科学研究。 再者,社会科学据说要成为真正提出有关社会现象的建议的主体,这种建议也就是对各种问题的回答。正确的答案——客观上有效的答案,可以根据逻辑的规律或原则来确定,但问题的提出则取决于一个人的兴趣所向,也就是取决于人的价值,取决于主观原则。现在正是兴趣指向的方向,而不是逻辑,提供了基本概念。因此,把社会科学的主观因素和客观因素分离开来是不可能的。客观的答案承受来自主观问题的意图。如果人们没有陷入潜藏在永恒的价值概念之下的腐朽的拍拉图主义,就必须依靠社会科学赖以存在的社会,即依靠历史,构想出具体体现在某一特定社会科学领域内的关于价值的某些见解。 社会科学不仅为历史研究所超过,而且社会科学本身也证实会成为具有“历史性的”科学。把社会科学作为一种历史现象的想法,导致了社会科学以及最终一般现代科学的相对化。结果现代科学开始被看作是一种历史地理解事物的相对方法,而这种方法在原则上并不优于其它理解事物的方法。 正是在这一点上,我们开始面对政治哲学的重要对手:历史循环论。历史循环论在其获得充分发展之后,由于下列特征而区别于实证主义:(1)舍弃事实与价值之间的区别,因为任何对事物的理解方法,不管是多么理论化,都包含着对事物的具
1、本站所有文本、信息、视频文件等,仅代表本站观点或作者本人观点,请网友谨慎参考使用。
2、本站信息均为作者提供和网友推荐收集整理而来,仅供学习和研究使用。
3、对任何由于使用本站内容而引起的诉讼、纠纷,本站不承担任何责任。
4、如有侵犯你版权的,请来信(邮箱:baike52199@gmail.com)指出,核实后,本站将立即删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