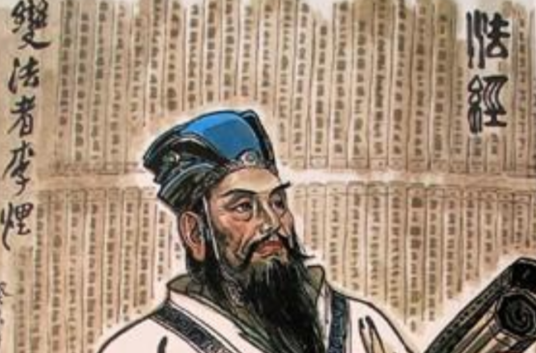-
法经 编辑
《法经》是一部魏文侯时李悝制定的律法 ,但它并不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律法,在《法经》之前,已经颁布了很多律法。它的制定者是战国时期著名人物李悝。 战国时期各国的变法很多,李悝在魏国魏文侯的支持下变法,其中之一就是制定了《法经》,约成书于周威烈王十九年(公元前407年)。该书已失传。据《晋书·刑法志》记载,《法经》分《盗》、《贼》、《囚》、《捕》、《杂》、《具》6篇。
中文名:法经
制定者:李悝
制定时间:公元前407年
相关记载:《晋书·刑法志》
内容:《盗》、《贼》、《囚》、《捕》、《杂》、《具》
《法经》共分六篇三个组成部分,即盗、贼、网(或囚)、捕、杂、具。前四篇为“正律”,主要内容是治盗、贼。《盗》法是保护封建私有财产的法规;《贼》法是防止叛逆、杀伤。《囚》是关于审判,断狱的法律;《捕》是关于追捕犯罪的法律;《杂》是有关处罚狡诈,越城,赌博,贪污,淫乱等行为的法律.《具》是一篇关于定罪量刑中从轻从重等定罪量刑之法。
据史书记载:李悝相魏,“竭股肱之力,领理百官,辑穆万民,使其君生无废事,死无遗忧”。《汉书·艺文志》注曰:“(李悝)相魏文侯,富国强兵”。由此可见,著《法经》是身为法家代表人物的李悝在魏国实行变法改革的措施之一,其目的是为了“使其君生无废事,死无遗忧”。从其内容上看,《法经》的指导思想就是“王者之政,莫急于盗贼”。再结合《法经》在《杂律》中对于“逾制”等罪名的规定。
《法经》与《十二铜表法》虽处于同一时代,但由于两者所处国家的历史、经济、文化等方面的不同,因此也在背景、渊源上呈现出巨大的差异。
《法经》产生于战国初期,正是中国由奴隶制社会向农奴制社会转型时期,可以认定《法经》及《法经》所代表的法律文化是建立在新兴的封建的自然经济基础上的,其内容是受封建的自然经济关系所制约的。
但是,对于《法经》是否存在及有关《法经》材料的真伪,始终有学者有疑义,认为李悝著《法经》,战国时代的法家著作及《史记》、《汉书》中都未提及,而且董说在《七国考》中所引的桓谭《新论》在南宋时就已散佚。因此怀疑《法经》是后人的伪作。对此,我国的一些学者,发表了一系列的文章系统的论证了《法经》的真实存在。其中何勤华教授的观点颇具代表性,他在总结以往学者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提出:“对于流传下来的文献史料,只要没有明确的证据证明其是伪造的,一般都应认可其真实性。对《法经》亦应如此。”笔者对此持赞同观点。
主要内容
《法经》的内容有六篇,即盗法、贼法、网(囚)法、捕法、杂法、具法。李悝的《法经》以盗法、贼法为首,是他认为"王者之政莫急于盗贼,故其律始于盗、贼。“盗”是指窃取财货,“贼”是指对人身的侵犯,也包括犯上作乱。有财货怕被人窃取,当然是地主阶级为多。侵犯人身,甚至犯上作乱,是对社会秩序的扰乱。这都是统治阶级所大防的。由此两篇法律可以看出,李悝的《法经》是为地主阶级的利益,以巩固封建统治秩序为出发点的。《网法》即囚法,是为了囚捕盗贼而设的,即"盗贼需刻捕,故著《网》、《捕》二篇。"据《唐律疏议》说,《囚法》讲的"断狱",即审断罪案的法律,《捕法》是有关"捕亡",即追捕罪犯的法律。
《杂法》据《晋书·刑法志》记载,是包括对"轻狡、越城、博戏、借假、不廉、淫侈、逾制等七种违法行为的惩罚。"轻狡"是指对轻狂狡诈行为的处罚,"越城"是对不从城门进入而翻越城墙出入城。《韩非子·外储说左下》载,梁车为邺令,其姐前去看他,至邺天晚城门闭,"因逾郭而入,车遂别其足。"梁车姐"逾郭"即翻郭城墙而入,她的弟弟以为犯禁而被刑。"博戏"即是聚众赌博。假即豭,指公猪。"借假"指男子寄宿于女子家,或称为"妻有外夫"。"不廉"指贪财受贿。"淫侈"指荒淫奢侈的行为。"逾制"指器用超过了规定的封建等级制度。这些规定,是为维护封建秩序而设立的。
《具法》是"以其律具为加减",即是根据犯罪情节和年龄情况,对判罪定刑加重或减轻的规定。
《太平御览》卷八二一引《史记》,《通典·食货二·水利田》。
主要体系
根据内容和篇幅,《法经》形成以下六大体系:
《盗法》是涉及公私财产受到侵犯的法律;
《贼法》是有关危及政权稳定和人身安全的法律;
《囚法》是有关审判、断狱的法律;
《捕法》是有关追捕罪犯的法律;
《杂法》是有关处罚狡诈、越城、赌博、贪污、淫乱等行为的法律;
《具法》是规定定罪量刑的通例与原则的法律,相当于现代刑法典的总则部分。其他五篇为“罪名之制”,相当于现代刑法典的分则部分。
李悝认为“王者之政莫急于盗贼”,所以将此两篇列为法典之首。《网法》又称《囚法》,是关于囚禁和审判罪犯的法律规定;《捕法》是关于追捕盗贼及其他犯罪者的法律规定;《网》、《捕》二篇多属于诉讼法的范围。
《杂法》是关于“盗贼”以外的其他犯罪与刑罚的规定,主要规定了“六禁”,即淫禁、狡禁、嬉禁、徒禁、金禁等。《具法》是关于定罪量刑中从轻从重法律原则的规定,起着“具其加减”的作用,相当于近代刑法典中的总则部分。
《法经》规定了各种主要罪名、刑罚及相关的法律适用原则,涉及的内容比较广泛,其基本特征在于:维护封建专制政权,保护地主的私有财产和奴隶制残余,并且贯彻了法家“轻罪重刑”的法治理论。《法经》的内容及特点充分反映了新兴地主阶级的意志与利益。
简朴性
所谓简朴性,是指构成古代法律秩序的法律规范体系并无科学的分类和层次,体现在法典的体例上就是诸法合体,民刑不分、实体法程序法不分。在《法经》和《十二铜表法》中我们可以清楚看到这一点。从现存有关《法经》的史料来看,《法经》的主要内容是以罪名为基础的刑法条文,如董说在《七国考》中引其《正律》中的内容“杀人者诛,籍其家,及其妻氏;杀二人及其母氏。大盗戍为守卒,重则诛。窥宫者膑,拾遗者刖。曰:为盗心焉。”但是,也并不完全只是刑法,《唐律疏议》中说:“《囚法》今《断狱律》是也,《捕法》今《捕亡律》也。”可见《法经》中也有相当于刑事诉讼法的内容。而且《法经》把维护私有财产权的《盗法》立为首篇,其中就不可能不涉及到对某些民事关系的法律调整,只不过一如我国古代法律的特点,是以刑事手段来调整而已。
从后人转述的只言片语中,我们仍是可以看到“拾遗者刖”这样以刑罚调整民事法律关系的条文,因此笔者认为推定《法经》含有调整民事法律关系的条文的结论是可以成立的。从内容上,可以认定整个《法经》是一部民、刑、刑诉诸法合体,而以刑为主的法典。从结构上看,李悝的立法思路也只是从其在魏国变法的最急切之处入手,先规定《盗法》、《贼法》;为了劾捕盗贼,再规定《囚法》、《捕法》;而后又将其他一些罪名统统收入《杂法》,最后将相当于后世的名例篇或刑法总则的《具法》列为尾篇。可见李悝在法典结构上还远未达到中国封建法律体系高峰时的水平,尚处于比较凌乱的阶段。
原始性及野蛮性
从整个人类文明史来看,《法经》与《十二铜表法》都是人类早期文明的产物。《法经》诞生于战国初期,正是中国由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过渡的时期。而《十二铜表法》更是诞生于罗马奴隶制社会的早期阶段。因此,两部法典便不可避免的带有人类早期文明原始、野蛮的色彩,并在其条文中显露无遗。虽然《法经》摆脱了《周礼》及《尚书·吕刑》中以刑统罪的刑法体系,改为以罪统刑,但是在对待刑罚的态度上却没有丝毫转变。
《法经》充分体现了法家重刑主义的思想。首先,它继承了《周礼》及《尚书·吕刑》中的各种肉刑如笞、诛、膑、刖、宫等,还规定了大量的连坐刑,如夷族、夷乡等;其次,“重刑而轻罪”。《法经》中称“盗符者诛,籍其家。盗玺者诛。议国法令者诛,籍其家,及其妻氏”还规定“窥宫者膑,拾遗者刖”,这样规定的理由是“为盗心焉”。以上两种表现,无疑使《法经》抹上了浓厚的暴力杀戮的色彩,散发出原始氏族征战与统治的血腥气息。
局限性
 李悝制《法经》
李悝制《法经》
在中国,法自始就是帝王手中的镇压工具,它几乎就是刑的同义词。而在古代希腊罗马,法却凌驾于社会之上,可用以确定和保护不同社会集团的利益。”在《法经》中,有“太子博戏则笞,不止则特笞,不止则更立”的条文,还有“犀首(将军)以下受金则诛”的条文,都不能说不严厉,对奴隶社会的礼制原则也造成了极大的冲击。但是这些“法治”措施击溃了奴隶制等级秩序,却又带来封建等级秩序。封建社会仍是等级特权社会。而法家的“法治”观最终仍是为“人治”服务,毫无民主性、平等性可言。
首先,《法经》是战国时期政治变革的重要成果,也是这一时期封建立法的典型代表和全面总结。《法经》作为李悝变法的重要内容,也是对这一时期社会变革的肯定。
其次,《法经》的体例和内容,为后世成文法典的编纂奠定了重要基础。从体例上看,《法经》六篇为秦、汉直接继承,成为秦、汉律的主要篇目,魏、晋以后在此基础上又进一步发展,最终形成了以《名例》为统率,以各篇为分则的完善的法典体例。在内容上,《法经》中“盗”、“贼”、“囚”、“捕”、“杂”、“具”各篇的主要内容也大都为后世法典所继承与发展。
第三、《法经》是维护封建国家的统治秩序,保护封建地主阶级利益的第一部成文法典。后来商鞅在秦国的变法,以及汉代的法律,都受到它的极大影响,它为历代封建法典所宗。
关于《法经》,法律史学界主要对以下问题存在不同看法;一是《法经》的真伪及明末董说《七国考》关于《法经》引文的真伪;二是《法经》的性质,即《法经》究竟是法典还是著作。
1、本站所有文本、信息、视频文件等,仅代表本站观点或作者本人观点,请网友谨慎参考使用。
2、本站信息均为作者提供和网友推荐收集整理而来,仅供学习和研究使用。
3、对任何由于使用本站内容而引起的诉讼、纠纷,本站不承担任何责任。
4、如有侵犯你版权的,请来信(邮箱:baike52199@gmail.com)指出,核实后,本站将立即删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