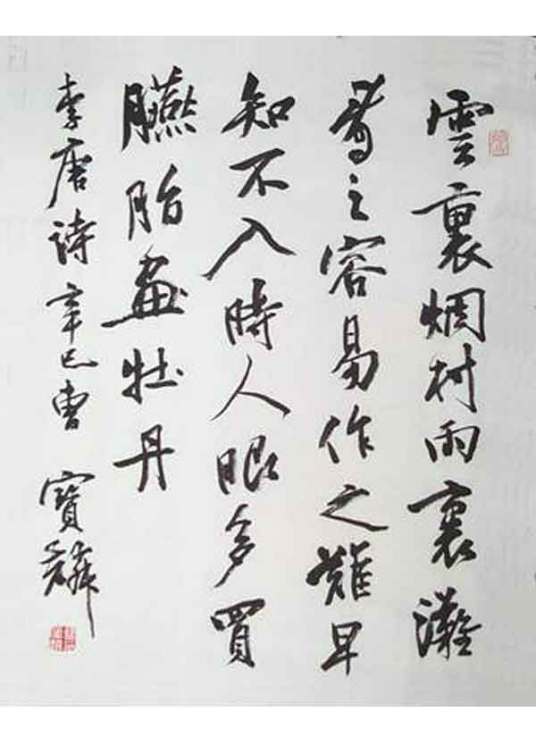-
唐论 编辑
《唐论》是唐宋八大家之一苏辙的政论文。该文论述一般历史现象,全文只有“唐太宗”三字及唐,而论唐又实际上是在论宋,是为宋王朝开救弊的药方。落笔甚远而紧扣中心,在短短的篇幅中,言在彼而意在此,有严密的逻辑性和说服力。
作品名称:唐论
作者:苏辙
创作年代:宋代
作品出处:唐宋八大家文选
文学体裁:古文
自周之衰,齐、晋、秦、楚,绵地千里,内不胜于其外,以至于灭亡而不救。秦人患其外之已重而至于此也,于是收天下之兵而聚之关中,夷灭其城池,杀戮其豪杰,使天下之命皆制于天子(1)。然至于二世之时(2),陈胜、吴广大呼起兵(3),而郡县之吏,熟视而走,无敢谁何。赵高擅权于内(4),颐指如意,虽李斯为相(5),备五刑而死于道路。其子李由守三川(6),拥山河之固,而不敢校也。此二患者,皆始于外之不足而无有以制之也。至于汉兴,惩秦孤立之弊,乃大封侯王。而高帝之世,反者九起(7),其遗孽余烈,至于文、景而为淮南、济北、吴、楚之乱(8)。于是武帝分裂诸侯(9),以惩大国之祸。而其后百年之间,王莽遂得以奋其志于天下(10),而刘氏子孙无复龃龉。魏晋之世,乃益侵削诸侯,四方微弱,不复为乱,而朝廷之权臣、山林之匹夫,常为天下之大患。此数君者,其所以制其内外轻重之际,皆有以自取其乱而莫之或知也。
夫天下之重,在内则为“内忧”,在外则为“外患”。而秦汉之间,不求其势之本末,而更相惩戒,以就一偏之利,故其祸循环无穷而不可解也。且夫天子之于天下,非如妇人孺子之爱其所有也。得天下而谨守之,不忍以分于人,此匹夫之所谓智也,而不知其无成者,未始不自不分始。故夫圣人将有所大定于天下,非外之有权臣,则不足以镇之也。而后世之君,乃欲去其爪牙,剪其股肱(11),而责其成功,亦已过矣。愚尝以为天下之势,内无重,则无以威外之强臣;外无重,则无以服内之大臣而绝奸民之心。此二者,其势相持而后成,而不可一轻者也。
昔唐太宗既平天下,分四方之地,尽以沿边为节度府(12),而范阳、朔方之军(13),皆带甲十万,上足以制夷狄之难,下足以备匹夫之乱,内足以禁大臣之变。而其将帅之臣常不至于叛者,内有重兵之势,以预制之也。贞观之际(14),天下之兵八百余府,而在关中者五百,举天下之众,而后能当关中之半。然朝廷之臣亦不至于乘隙间衅以邀大利者,外有节度之权以破其心也。故外之节度,有周之诸侯外重之势,而易置从命,得以择其贤不肖之才。是以人君无征伐之劳,而天下无世臣暴虐之患。内之府兵,有秦之关中内重之势,而左右谨饬(15),莫敢为不义之行。是以上无逼夺之危,而下无诛绝之祸。盖周之诸侯,内无府兵之威,故陷于逆乱而不能以自止。秦之关中,外无节度之援,故胁于大臣而不能以自立。有周秦之利,而无周秦之害,形格势禁,内之不敢为变,而外之不敢为乱,未有如唐制之得者也。
而天下之士不究利害之本末,猥以成败之遗踪而论计之得失,徒见开元之后,强兵悍将皆为天下之大患,而遂以太宗之制为猖狂不审之计。夫论天下,论其胜败之形,以定其法制之得失,则不若穷其所由胜败之处。盖天宝之际,府兵四出,萃于范阳,而德宗之世,禁兵皆戍赵、魏,是以禄山、朱泚得至于京师(16),而莫之能禁,一乱涂地。终于昭宗,而天下卒无宁岁。内之强臣,虽有辅国、元振、守澄、士良之徒(17),而卒不能制唐之命。诛王涯,杀贾(18),自以为威振四方,然刘从谏为之一言(19),而震慑自敛,不敢复肆。其后崔昌遐倚朱温之兵以诛宦官(20),去天下之监军,而无一人敢与抗者。由此观之,唐之衰,其弊在于外重,而外重之弊,起于府兵之在外,非所谓制之失,而后世之不用也。
(2)二世:是指秦二世胡亥,他在位三年,最后被赵高所杀。
(3)陈胜、吴广:秦朝末年农民起义的领袖,其国号“张楚”,起义最后失败,二人被害。
(4)赵高:本为赵国贵族,后入秦为宦官。秦始皇死后,他与李斯合谋伪造诏书,逼秦始皇长子扶苏自杀,另立胡亥为帝,并自任郎中令。
(5)李斯:秦代政治家。战国末年楚国上蔡(今河南上蔡西南)人。
(6)李由:秦相李斯之子。李由儿时起便与扶苏相交甚好,一同拜在蒙恬将军门下学习兵法。
(7)高帝之世,反者九起:九起叛乱是指:公元前201年十月,燕王臧荼叛乱,被俘获;利己反,被击走;七年,韩王信造反,被高祖平定;八年,赵国丞相贯高谋害高祖;九年,事发被杀掉三族;十年,赵国相国陈豨谋反,被镇压;十一年,淮阴侯韩信等反,被诛杀三族;梁王彭越谋反,被灭三族;淮南王黥布叛乱,被诛三族;十二年,燕王卢绾被告与陈豨勾结,被讨伐。一共九起。
(8)淮南、济北、吴、楚之乱:这里指的是汉文帝时候,因为诸侯的势力非常强大。到了景帝的时候,听取晁错的建议,进行削藩。吴王刘濞勾结楚、赵、济南、胶西等地的诸侯国,打着“诛晁错,清君侧”的旗号发动武装叛乱,最后被周亚夫平定,历史上称为“七国之乱”。
(9)武帝分裂诸侯:是指汉武帝吸取诸侯之乱的教训,对诸侯的领地进一步进行分封,削弱诸侯的实力。
(10)王莽:字巨君,魏郡元城(河北大名县东)人。汉元帝皇后王政君之侄。
(11)剪其股肱:是指除掉得力的助手。
(12)节度府:节度使是官职名,唐初沿北周及隋旧制,于重要地区设总管,后改称都督。
(13)范阳:唐藩镇名。亦名范阳镇、幽州。
(14)贞观之际:是唐太宗李世民的年号,一共二十二余年(627—649),李世民的清明执政也被称为“贞观之治”。
(15)谨饬:是指细心慎重。
(16)禄山:安禄山(703—757),营州(今辽宁朝阳)人。安禄山从一方节帅到身兼三镇,荣耀君宠达到顶峰。
(17)辅国、元振、守澄、士良之徒:是指李辅国、程元振、王守澄、仇士良四个人。李辅国(704—762),唐肃宗时当权宦官。本名静忠,曾赐名护国,后改辅国。
(18)诛王涯,杀贾:王涯,字广津,太原人。博学,工属文。
(19)刘从谏:范阳(今北京)人,唐朝藩镇割据时期任昭义节度使,以忠义自诩。
(20)崔昌遐:即崔胤。唐清河武城(今山东武城西北)人,字昌遐,一说字垂休。乾符进士。累迁御史中丞。
自从周朝衰微以来,齐、晋、秦、楚,疆土面积绵延千里,中央不能控制诸侯,最后到了灭亡而无法挽救的地步。秦国统一以后,吸取周朝诸侯拥有重兵最终导致天下灭亡的教训,就收缴了天下所有的兵器,全部聚集到关中,毁坏了诸侯的城池,灭掉各个国家的豪强,将整个天下的命运控制在天子的手中。就是这样,等到了秦二世的时候,陈胜、吴广号召百姓起义,那些郡县的长官纷纷逃跑,没有人能够抵挡。赵高在朝廷内专权,颐指气使、横行霸道,就是丞相李斯,也在经受很多酷刑之后,被腰斩于咸阳集市。李斯的儿子李由,担任三川郡守,虽拥有山河的天险,却不敢起来反抗。这两种祸患之所以能够发生,根源在于没有足够强大的外部力量足以制衡他们的力量。到了汉代之后,汉代吸取秦朝灭亡的教训,所以大封诸侯,然而,在汉高祖的时候,就有九个地方造反、叛乱,这些叛乱的残余,到了文帝和景帝的时候,就最终酿成了淮南、济北、吴、楚等诸侯国的祸乱。于是,汉武帝就在诸侯国中再分诸侯,进一步削弱他们的力量,防止大的诸侯国家叛乱的发生。然而,此后百年左右,王莽就实现了篡夺天下的目的,而刘氏子孙却不敢阻挠。魏晋的时候,就更加削弱了诸侯的势力,地方势力非常微弱,没有再发生叛乱。但是,朝廷的握有重要权柄的大臣和山间的平民,却是天下祸乱的很大的隐患。这些君主,他们在处理内外关系的时候,都犯了自取其祸的错误,但是他们自己却不明白。
天下权力的重心放在朝廷,就会成为“内忧”;反之,如果放在外边,就会成为“外患”。然而,在秦汉时期,不去探求造成这种局面的根本原因,只是交替吸取前朝的教训,用来迁就另外一方面的益处,所以祸乱就不断地轮回交替而没有终止。并且,天子对于国家的喜爱,与一般妇人、孩童喜欢他们自己的东西还不一样。得到天下之后就小心地守护它,舍不得与别人共享,这是庸夫之智啊!他们不明白,之所以守不住天下,正是因为不舍得与人分享的缘故啊。因此,圣人将要大治天下,外边一定要有握有重要权柄的大臣才能够震得住。但是,后代的君王,却处心积虑地除掉自己的爪牙,剪除辅佐的朝廷重臣,来实现国家的稳定,这已经是错误的了。我曾经以为,天下的形势,朝廷如果没有权威,就不能够镇压住地方上的豪强;外地没有握有重兵的权臣,就没有办法牵制朝廷内那些怀有奸邪之心想作乱的大臣。这两种力量要达到一种平衡,相互牵制才能够形成一种势,不能够削弱任何一方。
从前,唐太宗平定了天下之后,分封天下的土地,在国家的边境全部设置了节度府,范阳、朔方的节度使拥有十万全副武装的军队。对上足以制止外族发动的叛乱,对下足以镇压平民的造反,对内足以约束大臣们发动叛变。然而,那些担任将帅的大臣们之所以能够不敢叛乱的原因,在于朝廷也拥有足够多的兵力可以制约他们。贞观年间,天下的兵,分布在八百多个府内,而在关中就有五百个府,集中全国的兵力才相当于关中的一半。然而,朝廷大臣也没有乘机钻空子过分追求利益的原因,在于地方节度使的权力和兵力足够让他们感到震慑。所以在外的节度使,有周朝时候诸侯拥有重权在外的形势,并且更换设置都要服从命令,可以对他们的好坏忠奸进行选择。因此,国君就免去了亲自征战的劳苦,而天下也没有出现世代为官的大臣引发的祸乱。关中的那些府兵,与秦朝时候在关中拥有重兵的形势差不多,左右的大臣们都小心翼翼,谁也不敢做那些奸邪的事情。因此,上面没有被逼宫篡夺的危险,下面就没有被杀头灭族的灾祸。周朝时候的诸侯,因为没有中央的政府军的威慑,所以陷于叛乱却不能够自己制止;秦朝的关中地区,外边没有节度使的援助,所以最后才会受到权臣的胁迫不能够自立。集合了周秦的好处,却没有周秦的弊病,用形势来加以相互牵制和制约,朝廷内部不敢搞政变,并且外边也不会发生叛乱,没有一个像唐朝制度这样得体的。
而天下的人,并没有深究利和害的原因,一味轻率地吸取成败的历史,议论前代政治的得失。只是看到唐玄宗在开元之后,凶悍的武将拥有强大的军队成为天下的祸患,就认为唐太宗的政策是自大轻率不慎重的办法。议论天下事情以及胜败的形势,用来确定其法制的得失,还不如深究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天宝年间,府兵被分派到各地,主要兵力在范阳;到了德宗一朝,禁军在河北一带驻守,所以,安禄山、朱泚能够直捣京师,并且没有人能够制止他们,造成一败涂地的局面。最后,到了昭宗一朝,天下就没有一天安生日子了。朝内握有重权的大臣,即使像李辅国、程元振、王守澄、仇士良这样一群宦官,也无法控制朝廷的命运了。他们杀掉王涯、贾等人,自以为能够震慑四方,但是,刘从谏一讲到清君侧,那些朝臣们就惊恐并且自我收敛了,不敢再肆意横行了。这以后,崔胤凭借朱温的兵力,杀掉了很多的宦臣,取消了宦官监军的制度,没有一个人敢反对。这么看来,唐朝的衰落,弊病就在于外部藩镇的权力太大了。但是,藩镇的弊病,起源于府兵的外调,并不是府兵制的结果,但是,后代却取消了府兵制。
文章立意允当,结构严谨,行文简洁畅达,语言朴实淡雅。他的一生写的大量政治论文就具有这种特点。而且在短短的篇幅中,往往波澜起伏,委曲变化,说理透彻精辟,具有严密的逻辑性和说服力。
1、本站所有文本、信息、视频文件等,仅代表本站观点或作者本人观点,请网友谨慎参考使用。
2、本站信息均为作者提供和网友推荐收集整理而来,仅供学习和研究使用。
3、对任何由于使用本站内容而引起的诉讼、纠纷,本站不承担任何责任。
4、如有侵犯你版权的,请来信(邮箱:baike52199@gmail.com)指出,核实后,本站将立即删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