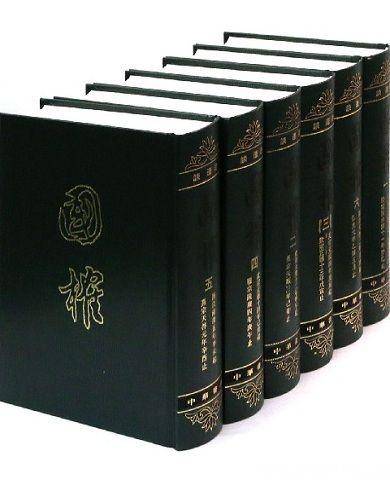-
国榷 编辑
《国榷》为记载明朝历史的私家编修编年体史书,作者谈迁。该书鉴于经史官员垄断了明历代实录,很多地方忌讳失实,而各家编年史书又多肤浅伪陋。谈迁寻访到各种资料,广征博引,力求征信。天启元年(1621年)始编著,初稿六年后完成。顺治四年(1647年)全稿被窃,他又发愤重写,以三十余年编成《国榷》一书,署名“江左遗民”。
《国榷》记叙从元文宗天历元年(1328年)九月明太祖朱元璋诞生,到顺治二年(1645年)五月清兵入南京、福王政权灭亡为止的三百一十七年间的历史。
其关于明代女真族发展状况及后金与明朝关系的记载,对后人研究大有裨益。书中还收集了很多有关农民起义的史料,作者对李自成起义军在北京的活动亲自作了调查,记于书中。此外,作者注意引用其他史学论著的评论,亦可供后人参考。所惜全书文字叙述过简,正德、嘉靖、万历三朝尤甚;有时前后内容失于照应,史实记述或有讹误。该书至清末无刊本,只有抄本,故未遭改窜。1958年由中华书局第一次排印出版。
作品名称:国榷
作者:谈迁
创作年代:明末清初
文学体裁:编年体断代史
类别:私修史书
卷数 | 时间起止 |
|---|---|
题记 | |
喩序 | |
自序 | |
义例 | |
卷首之一 | |
卷首之二 | |
卷首之三 | |
卷首之四 | |
卷一 | 元文宗天历元年戊辰九月至顺帝至正二十三年癸卯 |
卷二 | 元顺帝至正二十四年甲辰至二十八年丁未 |
卷三 | 太祖洪武元年戊申至二年己酉 |
卷四 | 太祖洪武三年庚戌至四年辛亥 |
卷五 | 太祖洪武五年壬子至七年甲寅 |
卷六 | 太祖洪武八年乙卯至十二年己未 |
卷七 | 太祖洪武十三年庚申至十六年癸亥 |
卷八 | 太祖洪武十七年甲子至二十年丁卯 |
卷九 | 太祖洪武二十一年戊辰至二十五年壬申 |
卷十 | 太祖洪武二十六年癸酉至三十一年戊寅闰五月 |
卷十一 | 太祖洪武三十一年戊寅闰五月至惠宗建文三年辛巳 |
卷十二 | 惠宗建文四年壬午 |
卷十三 | 成祖永乐元年癸未至三年乙酉 |
卷十四 | 成祖永乐四年丙戌至七年己丑 |
卷十五 | 成祖永乐八年庚寅至十一年癸巳 |
卷十六 | 成祖永乐十二年甲午至十六年戊戌 |
卷十七 | 成祖永乐十七年己亥至二十二年甲辰八月 |
卷十八 | 成祖永乐二十二年甲辰八月至仁宗洪熙元年乙巳五月 |
卷十九 | 仁宗洪熙元年乙巳六月至宣宗宣德元年丙午 |
卷二十 | 宣宗宣德二年丁未至三年戊申 |
(参考资料: )
历史背景
谈迁生活的年代,正是一个风雨飘摇的时期。明朝统治者消极怠政、宦官专权乱政、党争结社频频,天灾不断,农民起义此起彼伏,再加上清军不断叩关。值此国危的时代,“士习甚嚣” 的言论不绝于耳,怀抱着经世致用之大志的晚明士大夫们不甘朝野倾轧、世风日坏,期望凭一己之力,救国家与人民于危难之中。他们的出发点是好的,但愿望往往受现实的摧残,在农民起义的洪流和清军铁蹄的征服下,这批在野士大夫们被迫接受这样的身份转换,成为了明朝遗民,从此开始了对人生及未来的抉择和思考。谈迁就是这样一位“遗民”的代表,他亲历时代的巨变,思想发生了一系列新的转变,更迭的世局逼其发出“亡国不亡史”的疾呼。
谈迁对明朝史学的总体评价,见于他天启六年写作的《自序》。这篇自序,反映了谈迁对明代官方史学与民间史学的基本看法。可以看作是谈迁进入明史学之前对明史学编纂现状的一个分析报告。按照现代的科学研究模式,作者的问题意识越强,越能发现现状问题之所在,才能找到正确的努力方向。谈迁修史的直接动因是不满意晚明的当代史纂修事业。晚明时期,明史纂修成风时代。研究谈迁史学,应将之放到晚明明史编纂风中加以思考。谈迁写《国榷》的学术背景,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晚明的《通纪》续补风,二是晚明司马迁派考信史学的复兴。新史料、正宗的史实增加了,人们的眼界高了,相对地对明史的编撰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迫切需要编纂新的明史著作,故而晚明出现以《通纪》改编及续补形式出现的明朝编年史编纂热潮。谈迁编《国榷》正是在这一热潮影响下进行的。
文化背景
自古以来,修史总是作为一种“鉴往事,知来者” 的文化观念,根植于儒家文化体系中,无论治世,抑或是乱世,修史总能达到这样的目的,或扬长避短,或褒贬善恶。而明末清初正处于社会大变革的乱世时期,更是为大批史学家修史提供了坚实的思想基础和厚重的文化土壤,对国家和社会前途命运的担忧成为他们致力于撰史的动力,“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忧患意识,“促使他们对过去现实的反思和对未来走向的探讨”。 明清易代对于像谈迁这样的史家而言,不仅仅是变了天,换了皇帝,更是正统、道统如何继续维持的问题。对人生道路的抉择,对前途命运的担忧,在他们心中泛起了巨大的涟漪,经历了身心上的痛苦之后,思想上同样经受了一番冲击,必然希望从根源上找到明代社会何以走向灭亡。而修史则是他们表达这一心理变动最重要的方式。除此之外,作为一个史学家,以史言志可以说是清楚明白地表达他们政治立场的平台。然后站在史家的立场上,希冀探究明王朝由盛到衰的根本原因,并用自己儒家士人固有的传统道德规范去评价有明一代的统治得失。
作者背景
万历四十六年(1618年)至万历四十八年(1620年),万历皇帝行将入土,这不仅仅是明朝历史走向衰亡的时期,更可以说是谈迁人生道路的重要转折点。谈迁于万历四十六年(1618年)夏,谈迁赴京考试 再次失败之后,他并未像其它书生那样终其一生继续考取功名,而是认清了自己难以考中,于是自愿置身田园。 选择“缀耕之暇,汇为《兔园册》” 的耕读之路。壬戌夏,谈迁结识了钱而介,每个月都见面商讨编书事宜。之后分别,也多次书信往来。 从天启二年(1622年)夏,二人认识,每月会面,到天启四年(1624年)两人分手仍维持书信往来,谈迁与钱而介的交往使得其“废然返矣”, 由漫无目的耕读到有意识地读书,从吟诗作文到集中研习经史著作。
谈迁放弃了科考,也等于放弃了从政路线。既然不能在政治上为国家人民作出贡献,就干脆退而求其次,走学术研究路线。“经史是古代学术文化的核心,也就是读书人主要的研究方向”, 谈迁“少读国史,辄仰名阀”, 再加上晚明时期,涌现出了大多数在竞争激烈的科场中屡次败北,遂把毕生精力放在学术文化研究上的学者型史家,于是形成了一股治当代史的风气。史家群体的出现,使得修国史成为士人们引以为傲的事情,受这一时风的影响,在阅读了大量当代史著之后,天启元年(1621年)前后,谈迁终于选择了自己后半生的奋斗目标——治当代史。
编纂经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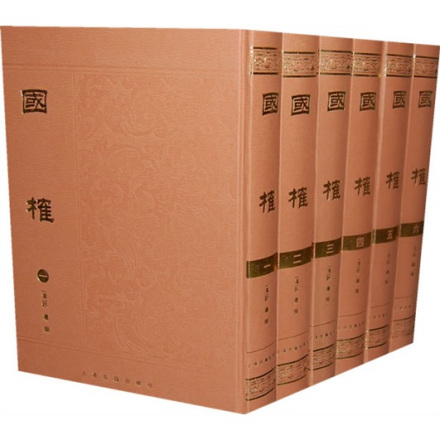 国榷
国榷
顺治四年(1647年),《国榷》全稿被窃,谈迁又发愤重写。顺治十年(1653年),谈迁应弘文院编修朱之锡邀请,携稿赴北京,访问前朝遗老、皇室、宦官、降臣等,阅读公家档案,重新校订《国榷》,以三十余年编成《国榷》一书,署名“江左遗民”。
书名来源
《国榷》第一稿已经失传,幸好谈迁的自序、凡例、朋友喻应益的序还留世,还有失稿后给钱士升写的信,尚可以对《国榷》第一稿有关情况作一推测。喻应益序明确称:“孺木《国榷》足以兼《尚书》《春秋》之盛事矣,尤天所必存之书也。”由此可见,原稿就称《国榷》。
明实录
《国榷》取材于明历朝实录,但又校正实录。因为实录“见其表,其在里者已不可见。况革除之事,杨文贞(士奇)未免失实,泰陵之盛,焦泌阳(芳)又多丑正,神(万历)熹(天启)之载笔者皆宦逆阉之舍人。至于思陵十七年之忧勤惕厉,而太史遁荒,皇宬烈焰,国灭而史亦随灭,普天心痛。于是汰十五朝之实录,正其是非,访崇祯十五年之邸报,补其阙文”。 可见明代历朝实录中,太祖、孝宗、神宗、熹宗各朝记载有失实、丑正、歪曲的毛病,崇祯朝没有实录。
明亡后,崇祯、弘光两朝实录,已无人顾及,谈迁不忍“国灭而史亦随灭”,他访求邸报、询及遗老,补齐两朝史事,寄亡国之情丁先朝史书的编修,自署“江左遗民”。这和常时留心国史典故之史家编撰史书的心情是有所不同的。
私家著述
《国榷》又广采溥引,遍览私家著述,择善而从,取舍严谨,秉笔公正,不以个人爱憎为务。他参阅“诸家之书凡百余种,苟有足述,靡不兼收” 。其中征引最多的有:雷礼的《大政记》《列卿记》,郑晓的《今言》《吾学编》,王世贞的《弇山堂别集》,薛应旗的《宪章录》,焦竑的《献征录》,高岱的《鸿猷录》;屠叔方的《建文朝野汇编》;徐学谟的《世庙识余录》,邓元锡的《皇明书》等等。所以,他编撰《国榷》虽据实录,但又不完全依赖。
第二,据事直书,信而有征。谈迁在是书《义例》中,认为“月日一时,是非千古”,下笔不可不慎。他对司马迁《史记》“据实以书”的直书精神十分推崇,明确表示自己著书要继承这一优良传统。这种直书精神在此书中随处可见。如朱元璋晚年大肆杀戮功臣之事,《明实录》只记某年某月某日某人死,至于因何而死,则隐讳不载,谈迁不仅将杀戮的事实如实加以记载,而且反复指责朱元璋“多所猜忌”“厉刑威读”的本性。对于建文帝,《明实录》也根本不承认,谈迁不仅恢复建文年号,而且真实记载了建文帝与明成祖的关系。对武宗的荒淫,神宗的贪,思宗的刚愎虚伪与好名不实,弘光的愚昧腐朽等等,都作了实事求是的记载,并视之为明朝灭亡的原因。特别需要注意的是,关于明末与清兴起这段历史的记载,当时具有很大的风险,因为清统治者对自己的祖先努尔哈赤原来不过是臣属于明朝的一名建州卫左指挥使这段历史讳莫如深,认为很没有面子。所以清修《明史》便隐去了这段历史。谈迁在《国榷》中,则毫不避讳,据事直书,甚至还直称之为“女真野人头目”。可见,他为了留信史于人间,早已将个人的安危置之度外。要做到据事直书,除了需要足够的勇气和胆识外,史料无疑首先必须真实无误,谈迁对史料的取舍标准是“人与书当参观”,即将人物本身与资料记载结合起来考察比较,择善而从,决不轻信。
第三,夹叙夹议,文笔简练。谈迁既要衡评、商耀历史,评论历史的是非得失便成为一个重要内容。在《国榷》中,他随时夹插了许多按语,或评或辩畅叙己见,颇多真知灼见。有的则是引用诸家之说,借别人的议论表达自己的看法。这部分内容不仅可以启迪人们对历史作出分析思考,而且也成为后人研究谈迁的史学思想和历史观的重要材料。《国榷》一书的文笔也很简练,作者自己在《义例》中称“宁洁无靡,宁塞无猥,宁裁无赘”。黄宗羲也说此书“按实编年,不炫文彩”。当然,此书一些地方亦有失之过简之缺陷,史实也有混之处,其中的一些观点在现在看来也并不正确。
客观真实
该书记叙从元文宗天历元年(1328年)九月明太祖朱元璋诞生,到顺治二年(1645年)五月清兵入南京、弘光政权灭亡为止的三百一十七年间的历史。
《国榷》写出了《明实录》因政治利益顾忌而没有写出的真相。如果分段来考察,《国榷》中对于明朝开国史的考证最费时间。明朝的开国史,尤其是洪武朝杀功臣之事,最为难写,问题最多。自晚明以来,朱国祯、钱谦益诸人,一直在关注这段历史。谈迁作为一个乡村秀才,自然不知道朱国祯、钱谦益在做这些事。当然,《明实录》是较为全面记录明朝历史活动轨迹的史书,所以,谈迁写《国榷》绕不过的。历史的真相,经常被各种利益集团无端蒙蔽,因此,要通过重读来廓清事实真相,还历史以本来面目。私修国史与官修国史的不同,某种程度是政治原则与历史原则的不同。
《明实录》的不足之一,就是掩饰真相,主要是洪武朝杀功臣之事,其次是靖难之役的粉饰。经过二次改修的《太祖实录》,确实编进了不少朱元璋欣赏燕王的故事,由此可以肯定,《明太祖实录》有关燕王部分记录,都是临时编制出来的,这就是典型的政治粉饰。这种政治粉饰,可以欺骗一时,但不可能永远欺骗历史。从这些事例中,谈迁总结出一个著名的观点:“史之所凭者实录耳,实录见其表,而其在里者已不可见。” 也就是说,实录提供的是表面事实,而缺乏内在原因的资料。或者说,实录中不少内容都是表面现象,更深层的信息,必须辅之其他材料来揭示。
纠正失误
《国榷》补充、纠正了《明实录》存在的失误。韩国历史学者金泽中将之概括为几个方面:(1)遗漏重要史实;(2)过于主观;(3)叙述错误;(4)记录疏略;(5)观点混淆。从以上的五个方面实录考证与补充例子来看,谈迁确实是下了功夫,作过考证的。《国榷》中所记事实,作为知识,经过了科学意义上的拷问,也更具有参考意义。也就是说,《国榷》突出的应该是实证精神上与参考价值上。考证显示的是研究水平,考据是一种历史研究。用考据解决的问题,数量不多,但成绩值得高度肯定。将实录与群书作一对比研究的人,谈迁是其中之一。在明末清初,能有机会阅读《明实录》,且作过详细研究的人并不多。《明实录》的政治性,使之不能完全原封不动地被使用,必须重新被拷问。在这种情况下,《国榷》无疑是判断《明实录》真伪的最好佐证材料。
补充不足
《国榷》可补明末三朝记录不足之缺。可考的《国榷》抄本,多是关于明末天启、崇祯、弘光三朝的。这种情况的出现是有一定原因的。明朝自嘉靖以来,出过不少明史,多写到嘉隆朝,间及万历朝。前14朝编年史已经有著作出版,自然不需要再抄了。崇祯朝、弘光朝的编年史,是谈迁《国榷》特有的。1958年版《国榷》六大册,仅晚明三朝就占了一册,可见内容详细程度。特别是崇祯十七年(1644年)至弘光二年(1645年)之间,内容尤为详尽。谈迁是当时人,有自己的感性与理性视角,这部分历史内容的选择,自然有其独到的史料与编纂价值。现存《崇祯长编》内容不全,《国榷》就有了独到的价值,也特别详细。特别是,清朝早期一段历史,明末李自成、张献忠起义,《国榷》有较为详细的记录。
史料检索
《明实录》有史料信息检索功能。与《明实录》的详写相比,《国榷》的特点是简略。这是不足,也是优点。如果《国榷》与《明实录》一样详细,就没有了《国榷》的地位。详略的不同,决定了它们的不同价值与不同的历史地位。今人如欲使用《明实录》材料,而又嫌实录部头太大、检索不便的话,完全可以先读一下《国榷》,然后再按图索骥,到《明实录》中找相应的更详细的材料。古代中国政府有一个规定,实录不能公开流传。《明实录》也一样,长期搁置在皇宫中。晚明以后,开始流传民间,有了多种抄本。但因为是政府之物,有政治风险,又因篇幅太大,所以,一直没有正式刊本。流传下来的,仅有多种抄本。尤其是实录是编年体史料长编,材料按时间顺序编排,没有详细的内容目录,更没有索引。所以,《明实录》的翻检与使用是十分不便的。在这种情况下,有一部简明扼要的《国榷》是十分迫切的。当年吴晗就是因为这个原因,而对《国榷》这部书表现出欣喜若狂之情。在《明实录》不能完全检索化的时代,《国榷》的检索功能是不能代替的。
史学家罗仲辉认为,谈迁受儒家正统思想的束缚,编撰《国榷》的目的最终还是为了维护纲常名教。所以在书中大力笔伐朱棣冒嫡夺位,鼓吹“帝统必不可违,世系必不可紊”。在明清之际民族矛盾十分尖锐的时候,还在纠缠朱棣是否“正出”,景帝应否让位的问题,其思想认识与同时代的王夫之、黄宗羲、顾炎武等人相比,显得落后而且迂腐。但他把朱棣篡改过的实录作了大量纠正,不仅暴露出封建统治者在争权夺位的斗争中表现出来的凶狠残忍,而且也给后人留下了部分较真实的历史记载。
书中叙事有的过于简略,有的事件前后记叙重复且说法不一。另外,封建正统史观、儒家天命论、佛道等迷信思想,在书中也有浓重反映。由于书中对清政府颇多谴责,当时成为禁书。
朱彝尊也说:“(谈迁)留心国史,考证累朝实录宝训,博及诸家撰述,于万历后尤详,号为‘国榷’。”对其书在订正史实尤其是辨证《明实录》之失上的功绩都予以称扬。明史大家吴晗评价其人其书“主要的根据是列朝实录和邸报,参以诸家编年,但又不偏信实录,也不侧重私家著述。他对史事的记述是十分慎重的,取材很广泛,但选择很谨严,择善而从,不凭个人好恶。”而谢国桢先生亦言其“编次谨严,颇有法度。”“记有明一代史事之书,取材之广,要以此书为备。”
《国榷》科举史料的记载较为系统和完整,具体来讲,大致表现为以下两个方面:首先,《国榷》科举史料的记载时间跨度较大且较为系统。《国榷》按年、月、日编成大事记,以编年的形式,保存了系统而丰富的科举史料。其次,《国榷》科举史料的记载较为完整。从笔者对该书科举史料的辑录情况来看,该书对应天和顺天的乡试主考、会试主考、殿试、庶吉士考选等四项信息,除少数几卷没有记载外,其余每卷都有系统的记载。
《国榷》也写出了《明实录》因政治利益顾忌而没有写出的真相,补充、纠正了《明实录》存在的失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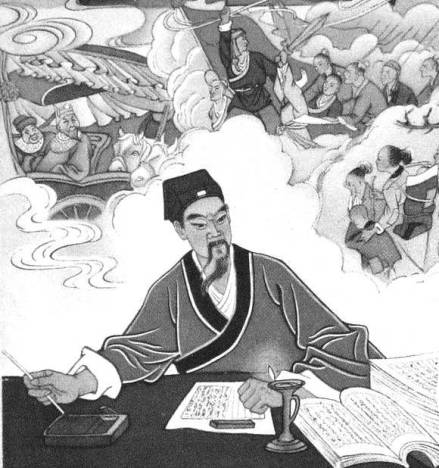 谈迁
谈迁
1、本站所有文本、信息、视频文件等,仅代表本站观点或作者本人观点,请网友谨慎参考使用。
2、本站信息均为作者提供和网友推荐收集整理而来,仅供学习和研究使用。
3、对任何由于使用本站内容而引起的诉讼、纠纷,本站不承担任何责任。
4、如有侵犯你版权的,请来信(邮箱:baike52199@gmail.com)指出,核实后,本站将立即删除。